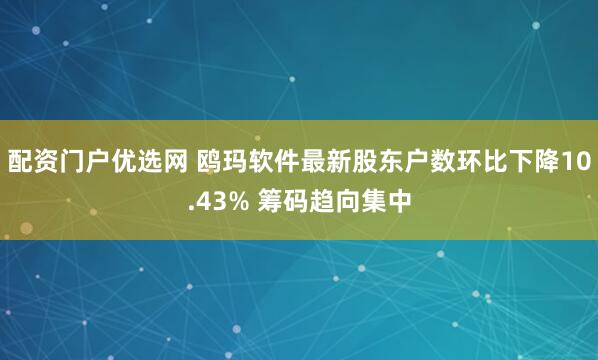文|星海配资门户优选网
编辑|星海
文|星海
编辑|星海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“皇帝纵情声色,不稀奇;但贪色与权力合流,才更具危险性。”
在历史传说与正史交错之间,汉哀帝与隋炀帝常被当做“色欲极致”的代表。他们的仕途、宠臣、政变、奢靡,似乎都与“欲色”纠缠。
汉哀帝与董贤的恩宠轨迹
董贤出身云阳,字圣卿,父亲董恭为御史。年轻时他在朝廷担任太子舍人。哀帝登基后,某日发现其在殿下传漏时容貌出众,便命人引见,并拜为黄门郎。从此,他进入皇帝视野,被调升多职,受恩宠日盛。他在宫中逐渐承担侍中、驸马都尉等职务,贵震朝廷。
展开剩余87%哀帝赐给董贤大量赏赐,妻子、女弟、亲属皆得封官受禄。他赐其第宅、重构府邸,在北阙下起大第,为其建造宫室,用品车马珍宝皆赐予其家。董贤常与皇帝同寝共枕,出入左右无所不至。在朝堂上,他的亲属、门户皆受到重用。
在《汉书·董贤传》中有著名一段:一次午睡时,董贤的身体压在哀帝的衣袖上。哀帝欲起身,不忍惊眠中的贤,遂割断衣袖离去。这便是后世“断袖之癖”的典故起源。史书称“尝昼寝,偏藉上袖,上欲起,贤未觉,不欲动贤,乃断袖而起”。这种恩爱至此,成为文学与文化长期引用的片段。
在《汉书·董贤传》中有著名一段:一次午睡时,董贤的身体压在哀帝的衣袖上。哀帝欲起身,不忍惊眠中的贤,遂割断衣袖离去。这便是后世“断袖之癖”的典故起源。史书称“尝昼寝,偏藉上袖,上欲起,贤未觉,不欲动贤,乃断袖而起”。这种恩爱至此,成为文学与文化长期引用的片段。
董贤的宅第、家族、亲族极度膨胀。他的女弟被封昭仪,仅次于皇后。他妻子、女弟、父亲、弟弟都被授官、赐爵。其家奴、家僮亦受赏赐。朝廷几乎为董氏量身铺设荣华。
在哀帝去世后,政局骤变。王氏外戚迅速反扑,董贤丧权辱命,一夕间从宠臣落为贬官。其家族被株连,其亲属被清洗。董贤被逼自杀,家族尽诛。这个由宠入罪的命运转折,成为“宠臣风险”的典型。他曾是皇帝心头宠儿,最终却被抛弃殒落。
奢靡政权下的隋炀帝
隋炀帝杨广在史书中留给后人的印象,一直带有奢靡、征伐、暴政色彩。他重游五经、置苑囿、修宫殿、骋车驾游,宫廷生活与巡游动线都浸润于豪华建造与人力耗用。史书中他“盛治宫室,穷极侈靡”之语广为引用。正史《隋书》《隋书·炀帝纪》详细记其宫室工程、苑囿布局、宫庭建筑规模之宏大。
在这些奢华之中,宫妃嬖宠与美色传说也不断为后世所谈。通俗历史文稿写他在宫中罗列妃嫔、广设后宫制度、令宫女穿漏体衣等情节。这些描述虽多见于后世笔记与小说体例中,却反映出他性欲与宫廷资源整合之间的张力。
他的宫殿建设、园林陵寝设计、珍宝装饰、车驾游幸,都涉及大量动用国家资源。诗人李商隐《隋宫》等作品对其奢华有感言,描写其御苑花木、宫墙丽饰、结构奇观。在诗中,他的一切景致都以欲望铺陈。
对其美妃、私人性欲活动的具体细节并不详。正史更多记录其建宫、修苑、迁都、驳议等行为。学界近年对隋炀帝形象有再思考,认为负面形象有时代叙述偏向,《隋书》注本身带有后世评价成分。在奢靡政策与宫廷欲望之间,他的“色”常被政治批评合并。
隋炀帝也有荒淫传说被文学加工,如《隋炀帝艳史》《隋杨传》《隋遗录》等小说与笔记书中,关于他对庶母宣华夫人的倾慕、妃嫔无数、夜夜笙歌的情节颇多。这些作品引用部分正史事迹,却加入大量虚构。这些虚构情节在民间传播甚广,使其“色魔”形象深入人心。
在权色角度上,他的皇权操作、资源调配、副宫置布、妃嫔晋升、宫室建设等都是权力行使形式。妃嫔不仅为性对象,也承担政治代理、后宫势力、家族利益、调度反馈功能。他的“色”不单是私欲,更与政治资源配置、官选制度、驸马制度、宫廷结构紧密关联。
从宠臣陨落到荒淫之君
董贤的兴起与陨落,是“宠臣命运”的经典缩影。他曾是哀帝身边无可替代的存在。宫廷中有传说,哀帝与董贤同床共枕的情境非稀罕。某次睡梦中,董贤压着皇帝的衣袖,哀帝怕惊醒他,遂割袖起身——此“断袖”典故流传千年。这个故事虽简短,却在后世对皇帝与宠臣关系的想象中占据极重地位。
在权力入口处,他一跃而上。朝中有人指出,哀帝为了奖赏董贤,曾将御史、吏部、门下、巡守等多重职位授予其近亲,一步步将其家族捆绑进入权力机器。他无须动刀斩将,就在文书背后调动国家资源,为宠臣铺路。
权力崩塌常在瞬间降临。哀帝亡故,当权者急速反扑,董贤失宠、被去官、被株连其亲属。惊鸿一瞥的宠信,在王莽外戚与王氏集团回归之下,迅速消解。宠臣曾被捧上云端,转眼便被拖入深渊。
反观隋炀帝,他不是靠独宠一人建构权色帝国,而是用制度与资源浸透宫廷的每一角落。从宫殿建设到苑囿布置,从车驾游幸到驿站铺设,他几乎把“美”与“欲”变为国家工程的一部分。他建西苑于洛阳之西,周围数百里,内设人工湖、山石、水道、楼阁——一座宫室王国。在那片园林内,妃嫔、美人、灯火、乐声交织成隋炀帝的欲望演出舞台。
他还大兴舟舰,游幸江都。宫女、歌妓、妃嫔随行数千。某些通俗版本说他令游艇如长龙、妃者成行,船体豪华无匹。史书中记他“盛治宫室,穷极侈靡”,虽非详列每个妃嫔行为,但这一带动天下资源为宫廷服务的行为,本身便带有“权色合流”的特质。
在他频繁的南巡北伐、宫廷建设与劳役征调中,“资源优先服务于宫廷享乐”的意图不断显现。妃嫔制度、后宫权力、选美制度、宫廷赏赐,均可能成为满足性欲的渠道。他拥有的是整个帝国的“后宫舞台”,而非单一宠臣的故事。
董贤故事中那种“一对一”的宠臣关系,更容易凝固为“色”典型。而隋炀帝那种“大范围宫廷欲望体系”的权色融合,则是一种结构性、制度化的“欲望帝国”。
两者比较,董贤—哀帝关系像一本浓缩的宠臣寓言;隋炀帝的宫廷欲望像一部庞大的现实舞台。在董贤故事中,人性与情感被放大;在炀帝故事里,权力资源、国家机器、社会劳役都被卷入欲望。若从“色”与“权色合一”的角度看,隋炀帝的欲望结构可能更具张力。
边界、争议与后世语境
在《旧唐书·本纪第六 则天皇后》卷中,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冬十一月壬寅,则天将大渐,遗制祔庙、归陵,令去帝号,称则天大圣皇后;其王、萧二家及褚遂良、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,咸令复业。是日,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。”这一段话常被后世用作武则天晚年“为褚遂良等人平反”的依据。
从这一诏令文本看,它确见于正史,是她“将大渐”之时所立的遗制一部分。那条“咸令复业”的命令,在当中明确点名王、萧、褚、韩等族人或受累者子孙。那意味着,她在生命末期愿意以制度途径,恢复那些被牵连者的官爵或名誉。这是正史最确切可据的“平反行为”记录。
不过,这条命令的具体范围、方式、时机和对象,仍留有历史模糊空间。例如,“缘累者”一语意味受牵连的子孙亲属,并不一定指褚遂良本人当时仍在朝中;“咸令复业”也可能是一种恢复资格的行政命令,不同于重任官职、重获实权之举。
与此同时,在正史中,褚遂良的生平中确有被贬、流放、再起的记录。他曾因在册立武后、废立后宫政策中持异议,被流放为潭州、桂州,后在武则天末年得到赐复官爵。正史中称“神龙元年,武后遗诏复其爵位”。这一赐复被视作她晚年对其往日牵涉的一种纠正。
但从史料面看,将“遗制复业令”与“临终心念”之间完全划等号并不安全。正史中,这条诏令被置于遗制文本整体之中,紧连“去帝号”“称后”“祔庙”“归陵”等内容。那表明,它更像一件身后事安排的一环,而非专为某人情感式的“临终平反”动作。
历史写作中必须保留张力、承认边界。那条“令复业”的正史文本是真实存在的;其是否代表武则天“念念不忘某人”的深情垂悔,则还需要更多材料来证实。
我们可以肯定:在死亡前夕配资门户优选网,她愿意在制度层面为受累人家恢复体面;但无法确认她在那刻心中是否有某一个人占据主导位置。
发布于:北京市富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